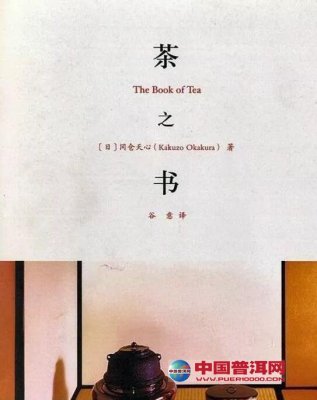普洱茶命名的起源,被采纳最多的说法是因为普洱府的建立。1729年(大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今天的宁洱县设置了普洱府,普洱茶因为在此交易、流通因而被人所熟知。普洱茶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无法令人满意,解释起来往往也令人困惑,就这一点,早在道光年间,阮福(1801—1875)就强烈地表达过。
我们一开始筹备要出这本《一本书读透普洱茶》的时候,多次向周边普洱茶达人征集意见,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问问他们本人对普洱茶知识阅读的印象,到底有哪些篇章是不可错过的?哪些是深深影响过自己的?哪些是重要,但对自己毫无指导价值的?
上百位受访者,都会谈到阮福所写的《普洱茶记》,一些人甚至只记得这篇,至少有10多个人脱口就能背诵出文章开篇文字:“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一个主要原因是好用,实用,易传播。
这份产品说明书太漂亮了,区区800余字就能把普洱茶系统地介绍清楚,从产地分布,采摘时令,产品称呼,制作标准,成品重量以及形式都有涉及,商家稍加修改,换成现代语言就可以直接做成自己的产品说明书。
阮福不是云南人,他写这篇普洱茶的时候,是站在京师立场上说话,告诉京师里面的人,你们喝到这个贡品,生长在何方,滋味如何,是怎么生产出来。
阮福不是普通人,他的父亲阮元是清代名臣,经学大家,当过云贵总督,对云南文化有过大贡献。现在大名鼎鼎《爨龙颜碑》,在阮元没有鉴定之前,一直都被当做洗衣板使用。
阮福在其父指导下,系统研究过云南人文地理,著有《滇南金石录》。阮福不仅传承有其父考据的功夫,也继承了他点石成金的眼光。碎片化的普洱茶,被阮福串成了绿宝石。阮福同时把说法不一的古六大茶山,正式明确下来,沿用至今。
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不过是记载了普洱茶与云南地理的对应关系。
清乾隆年间的进士檀萃在《滇海虞衡志》里说:“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日革登、三曰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
不过,檀萃话说得好听,但他已经找不到普洱茶繁荣的证据了。“普洱茶名重于天下”可能是更早的人说的,被檀萃,阮福沿用下来。
阮福从贡茶案册与《思茅志稿》里转述了一些他比较关注的细节:1、茶山上有茶树王,当地土人采摘前会祭祀;2、每个山头的茶味不一,有等级之分;3、茶叶采摘的时令、鲜叶(芽)称谓以及制作后的形态、重量和他们对应的称谓等等。
《普洱茶记》因为多了这些料,便成为普洱茶乃至中国茶史上著名的经典文献。
而其祭祀茶树王的民俗则被民俗(族)学家、人类学家更大范围内精细研究,甚至被自然科学界引入作为证明茶树年龄的有力证据。在普洱茶大热天下后,《普洱茶记》再次被反复引用和阐释,同名书更是多达几十本,其核心也不外乎阮福所谈三点细节最大化。
比如讲究一山一味,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茶思路。
一是用正山纯料制作普洱茶,二是把各山茶原料打散拼配做成普洱茶。就普洱茶历史传统来说,前者一直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老字号,比如“同庆号”,“宋聘号”。这些老字号后来虽在在云南境内消失了很多年,但他们的后人(也许并非如此)在近10年的时间里,又借助商业的力量把它们复活了。
令人惊叹的是,经销这些老字号的外地茶庄还健在,香港的陈春兰茶庄(1855年创建,是目前中国最老的茶庄)以及其后人吴树荣还在做着普洱茶营生,市场上的正宗百年号记茶几乎都出自“陈春兰”茶庄。
我们在此分拆信息:1、普洱茶在百年前就有百年店。2、普洱茶讲究出生地,也即正山。3、普洱茶有采摘时间,阳春。4、以“细嫩白尖”为上。5、色金黄。6、汤红且芬芳。7、当时就有假的同庆号。
然今日看到的许多“同庆号”非细嫩白尖芽茶,而是粗枝大叶居多,与内飞严重矛盾,内飞文字自然是真,茶就不好说,到底是当年的假货,还是当下的,不得而知。昔日作为真假判断的内飞,多年后依旧是有利的证据,茶饼逃不过历史的逻辑。
如果说,这是中国古老语境下的特色产品传统的话,那么拼配茶就完全是一个西化的概念。它来源于英国人掌控下的印度茶,而非中国。我们的传统虽然讲究味道殊同,但只是个人经验和口感判断,而非建立在对其香味、有益成分的生化研究上。简而言之,我们只有茶杯,人家有实验室。
印度茶能够异军突起,就在于英国人采用了不同原料的拼配混搭,把茶叶香气、滋味、耐泡度都提升到了新的层次。正是因为拼配技术,诞生了像立顿这样的大公司。1900年后,华茶处于全面学习印度茶的阶段,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拼配茶是他们学习的主要方式。1930年代,李拂一创建的佛海茶厂(即勐海茶厂)、冯绍裘创建的凤庆茶厂(演化成滇红集团和云南白药红瑞徕)走得都是这一理念,更不要说现当代的这些改制后的老国营茶厂以及他们培养的技术人员和他们之后创办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茶业公司。
纯料与拼配之争会左右着普洱茶的市场,但在品牌力量没有形成时,追求某地与某茶对应关系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普洱茶与老普洱县(今宁洱县)对应关系。
宁洱县成为普洱茶集散地后,当地茶并没有没有享受到普洱茶产业带来的太大好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不认可此地普洱茶。罪魁祸首居然就是阮福的《普洱茶记》。阮福说,宁洱并不产茶,其实这个地方在道光年间绝对产茶。
阮福没有到茶山的毛病,感染了许多人,茶学大家李拂一(1901-2010)在1940年代、庄晚芳(1908-1996)在1980年代都延续这个说法,哪怕是2000年前后出版的许多普洱茶著作,也还有人继续说这里不产茶。
历史话语的力量,当下还在发挥作用,太多人懂得利用历史来增加文化筹码,但历史也有被架空的时候,这考究每一个人的智慧。
即便是有阮福的《普洱茶记》在,在中国,也很难找出哪一类茶会像普洱茶这样缺乏完整的表达,主要原因在于,普洱茶的话语被历史、地域、人群以及商业稀释,显得零散而混乱。
具体而言,典籍与历史中的普洱茶与当下所言的普洱茶,并非一种承接关系,普洱茶的原产地以及其主要消费地的人群长期以来各自表述,难以取得共识,而商业力量的崛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洱茶的面貌、工艺乃至存在形式,这些都增加了对普洱茶的认知成本。也因为如此,普洱茶反而显得魅力四射,让人横生重塑欲望,这当然也是我们角逐普洱茶书写的主要动因。
认识普洱茶的常规路径,往往与历史话语有关,这也是早期和当下研究者角逐最多的领域。他们手胼足胝、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的普洱茶时代,在遥远的边陲云南,能够调动的典籍(汉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可谓麟角凤毛,有限的云南茶信息只有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放大镜,才能一步步被挑选并还原。(文|周重林,《茶业复兴》出品人,著有《茶叶战争》、《茶叶江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