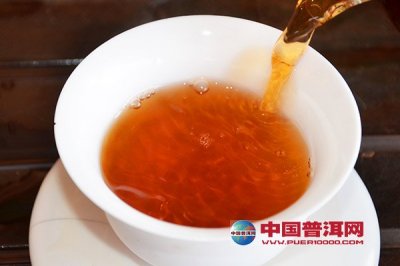八七年底,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八八年,台湾茶艺界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当时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市场受香港影响很大。
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大量老茶不断涌现。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更多也不知其所以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
时间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台湾茶艺界就已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亦是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时刻。当时的台湾、香港及东南亚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现传统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门等主要在茶楼饮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数几家有较专业的各式普洱,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一般市场上受香港影响很大,入仓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称谓不胫而走。
追寻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约过了二、三年的蛰伏,接着是黎明前暗涛汹涌期。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
但由与会各专家学者及业界提出的论文、会中讨论的内容,加上会场四周及茶叶街逛览,发现所呈现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数商店可买到渥堆的普洱茶砖,请了李松青、张顺高、王郁凤等喝咖啡,但我们谈的是陈年普洱茶,愈陈愈香的东西,他们却完全停留在绿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鸡同鸭讲”感慨,不过,邓时海带来的一颗末代紧茶,给曾经在云南做过茶,移居美国的楼杨丹桂女士相当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论文,而王郁凤的论文,亦提及清宫普洱等论证让台湾来的寻根茶人感受到异中有同的观念。
包括王郁凤的《普洱茶与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学年轻讲师温一波提出他走访的茶马古道记实,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历史中,均发挥相当大的魅力,但当时并不被大会所重视,有些论文如茶马古道即使后来出论文集仍未收录,但这也是促成我却追寻茶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讨会空档,立即驱车赶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鸟道],走在崎岖的石板上,正值夕阳西下,一轮夕阳高挂,遥想当时普洱茶还未兴盛状况,真的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感触。
当时为了争普洱茶的原乡,继思茅之后,西双版纳也在首府景洪配合每年的泼水节盛会接续举办[茶王节]活动,并展示了一些古老普洱茶照片,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都成为台湾茶人曰后寻根的主要线索之一,从点、线进而面,逐渐的串连起来,这亦是后记。
首度参与普洱茶盛会,台湾共有十五人与会,声势相当浩大,事后证明亦是推广普洱茶最有力的生力军。当时在街上买到了《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这本书,经过影印后传阅,成为来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四年进军古六大茶山之一易武重要的线索。
这本选辑可贵之处,在于集结了许多散佚的古六大茶山资料,包括易武的断案碑、老茶庄照片、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忆(是由已故倚邦最后一位土司曹仲益记录的),另外,还有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蒋铨的古六大茶山访问记,上面名列了我们手上有的老茶饼,包括同兴、同庆、同昌等,上面的资料注明是在易武街。
来年再度上路,由当时的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领军,先出席在昆明举办的国际茶文化节活动,与勐海茶厂老茶厂等亦是漏夜长谈,一阵的追问,另一重点锁定在易武,当时当地导游根本没听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可游之处,还不解的骂我们神经病,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易武实在地处偏僻,无旅馆等,第一夜选择了最近的孟仑,睡一间小旅舍,我、何健、吴芳洲摸黑进入颇具规模的植物园,发现一间宿舍亮灯,竟然不分青红皂白闯进去,没想到是找到宝了。
当时的主人是一位研究员,工作之余靠搜集蝴蝶标本增加收入,在聊天中,他告诉了我们其家人是易武人,早期制饼完全是手工,有木模和石模,日后何健找到老的“揉茶石”,和这次的夜访偶遇有很大关联。
就在那一天,踏入易武老街的那一刹那,我被震撼住了。
当时易武乡公所的小郑(郑军民,十多年后今天,已高升为易武乡副乡长。当时及之后几年,他对我们帮助相当大,带着我们出入落水洞等地,为人热诚,又毫无怨言,对他心中只有感激)看到一群“蕃仔”来到,他抱怨说,这些居民饭都吃不饱,您们是来干什么的。
就在公元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时任易武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吴正金,副乡长李家能等人被这群不速之客也惊扰到,不到百人的村民更是以相当惊讶的眼光,看着这群[猴子]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如今,这群猴子,却是孙悟空的金棒七十二变,将易武变成繁华小镇,这恐怕是当初这些居民想都没法想的,造化弄人,却也从此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普洱新市集)。
由副乡长李家能找来已退休曾任易武区区长张毅,解说易武的现况及所遗留昔日老茶庄辉煌年代景观,由于他老人家当时正在写乡志,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数据,由其一路导览,使得我们这一群虽第一次踏入被形容是“蛮荒”之地的小镇,却着实有入宝山而归感觉。
在老乡长解说着一世纪前名扬中外的茶庄时,又是钱利贞宋聘号、又是同兴号,又是车顺号,当时已有[众里寻他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感觉。清朝的[瑞贡天朝]匾额,就是在这一趟挖掘出来,后来在混沌年代,还有人趁机做出[朝天贡瑞]茶饼,令人啼笑皆非。
据张毅后来自己写的记录如此形容着“他们边看、边问、边记,还拍照,谢谢之声不离口,连用餐时间前几分钟,都不放过,问这问那…,曾至贤、陈怀远还把我向他们作的介绍材料,逐一的翻,四筒胶卷,全部拍完(当时尚未流行数字相机),带回台湾又用计算机打印出来,这成为他们这次考察最大收获。
不错,就是这份数据,光是用计算机打字,就花了我二个多星期时间,后来所有普洱茶书的资料,都是来自我搜集及不眠不休漏夜打的这份资料,可惜,均未向他们收取费用,否则应可收回一些成本,毕竟这是相当大心血,而大部分引用的人却连一声感谢都没有,让人有遗憾的感慨!
当时的易武,实在是荒凉,两条街,一条是老街,一条是让主要干道,一间小吃店,几家杂货店,几乎无外人沓至,有着茶人胸怀的吕礼臻、何健等感慨万千,他站在街头遥望着黄沙滚滚的昔日老街、茶马古道,心中许了一个愿望,那就是重新恢复传统七子饼茶的制作方式,让易武有第二春。
现在到易武逛览,犹如普洱茶风起云涌般,已是相当繁荣,但您觉得很难想象,当初易武的模样,当时落脚这个小镇,晚上是没电灯的,还要点烛火挑灯夜战,洗澡更是只能利用三更半夜,穿着短裤,躲在古井边,迅速以类似军火战斗澡方式解决,生活及交通等不方便,比起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