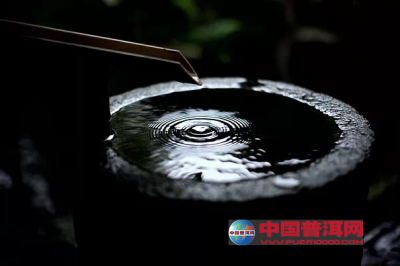对泡茶器而言,通常用得多是壶和盖碗。壶像是中年持重的男人,内压大、浑厚、出水慢,汤稠而蕴藉——熟普、红茶这样完全发酵的茶,用壶,是稳对稳,一脉相承地向内走;而盖碗,开放、敏锐、起伏大,像是一个聪慧而善言的女子,只要她能感受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单枞、岩茶,这类半发酵层次丰富的茶,用盖碗,可以演绎得姿态万千。用心观察,这两种器的选择,往往也代表了两种性格。但是也可能同一个人,这段时间用壶,过段时间用盖碗,是心境改变的外化。有一段时间,我不仅用壶,而且用水平壶,盖子盖上,从豆大的壶嘴入水——壶拎高一点,把水流拉成一条线,穿针一样,直直慢慢地落到壶嘴里。这样的方法,内压更大,近乎于萃取,哪怕是最后一道茶了,滋味依然饱满。那段时间,我很自闭,很多话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决定不说了。最终发现很多事情,最好的表达,就是不说。
还有一种用得不多的,就是碗泡:用一只有流的大碗,或者功力够,就用平常的碗。完全无遮挡,不闷不盖,这句话说来,就像是“随便说,畅所欲言”一样难说。因为无界限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你没有依傍,得靠你自己。比如绿茶这样娇嫩不发酵的茶,要还原其甜美又要不破坏其鲜嫩,已经近乎于一句禅机,不可说,一说就破,也不可不说,不说……不说就没茶喝。而且既然说了,就要点到,温度要够,不能用降水温这一偷懒的办法,像是拒绝,温和而坚定。器具是敞开的,内力是凝聚的,水温是高的,速度是慢的,一碗水端平,端的是,不容易。有次看老古用碗泡古法制作的恩施雨露,针形绿茶,碗泡碗出汤,分汤杯杯均匀,喝到嘴里,清甜缭绕如见青山绿水。最后的叶底,不焦不黄,如刚采摘的鲜叶。这话说的,圆满。
如果说泡茶器是说话的一个态度,那么杯子就是措辞,或者口音。薄胎白瓷聚口杯,就是普通话:标准,不夸大不缩小,对茶汤的还原最接近真实状态。初学泡茶者必备,说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不能词不达意。准确,是说话的第一步。
除此之外,不同的器形、釉色、烧结温度,可以变幻出千变万化的茶之语。一次,喝蜜兰香单枞,用一只柴烧倒钟杯和一只青瓷斗笠杯做实验——柴烧倒钟杯入口:涩、滞、挂喉;而青瓷斗笠杯:滑、香、爽口。这是因为柴烧杯不好吗?不是。是因为单枞生烈香猛,单枞就是《红楼梦》里的尤三姐,美艳带刺——要是不依着侬的脾气,就是杏目圆睁柳眉倒竖;要依着侬的脾气,把语气放和软,才能亲近香泽。
所以青瓷是平滑的,斗笠的器形是敞开的,好说好哄,茶汤在里面才肯显露娇媚温柔。真真是,从来佳茗似佳人。但是同样是这两个杯子,用来喝熟普,青瓷斗笠杯就不够力道了——熟普已经够圆滑,柴烧倒钟杯深聚的形状,恰好箍得住这一汪圆滑,把成熟立起来。而来自柴窑火气的刚劲,把厚度又强调出来,恰是一句听上似是而非的话,把意义抓了出来,然后得到深化。有时候这样的茶喝到嘴里,往往都不像是水,而是扎扎实实的食物,比如像甜枣香的羊羹。
不妨玩玩看,好玩;不妨说说看,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