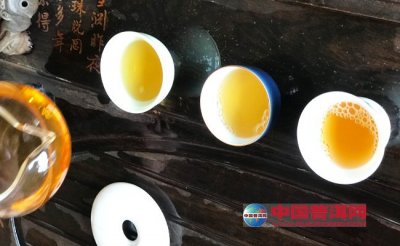凉夜,孤灯。
在外行走,虽说眼界大开,但还是很辛苦的;今晚,坐在家里的茶几前,只想品一杯香浓四溢的茶。伴随着茶氤氲的香气,随意点击着一个个网站,无意中看到一篇茶的故事,关于茶的一世情缘的回忆……我把故事转贴上来,与朋友们一起品茶品人生。
第一次见她,梳着一个马尾辫,穿着碎花的布拉吉,一身的青春,满脸的阳光。
车间主任领着她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你师傅,以后你就跟着他吧。 她叫了声“师傅”,声音脆脆的嗲嗲的。他抬了抬眼睛,瓮声瓮气的说了句:换工作服去。
她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学得很快,而且很活泼,总是喜欢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或者无缘无故的笑起来没完。她笑的样子很好看,每当她笑起来,都会引来车间里小伙子们热辣辣的目光。这时候,他就会冷冷的崩出两个字:“干活!” 她总是会带着几分天真,几分稚气的认真地看着他的脸,认真地问他:“师傅,你为什么总是绷着脸,你不会笑吗?”他面无表情地看她一眼,低下头继续干活。她就会咯咯的笑上好大一阵。
他不是不会笑,而是不能笑,不敢笑。在她来之前,厂党委书记特意把他叫去,严肃的通知他,带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是政治任务,是领导对他这个车间团支部书记的信任和考验。是光荣艰巨的。
她快乐的说着、笑着,他闷闷的低头干活。两个人都习惯了。突然有一天,她没有来上班。
他仿佛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觉得周围空落落的,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车间主任说:她病了,你这个当师傅的去看看他吧。他有点犹豫,主任又说:关心徒弟,这也是任务。
于是,他生平第一次走进了女孩子的房间。
她有点意外,有点感动,很小心的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袋,很珍惜的拿到脸前嗅了嗅。
“师傅,你是我的贵客,我隆重的请你喝茶。”
他在电影和小说里看到过茶,只知道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耽迷的一种东西。他想拒绝,但是看到她殷殷的样子,拒绝的话,没有说出口。
电炉上的小铝壶冒出的蒸汽,散发出奇异的味道,怪怪的。他坐在那里,心里泛出一种感觉,也怪怪的。她把一杯茶小心翼翼的端到他的面前,炫耀的说:
“快尝尝,这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上等的茶叶,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没有泡到他就喝了一口,热辣辣的苦、涩,,他皱起了眉。
她又咯咯的笑了起来:“不习惯?”
茶在当时是一种奢侈的物品,只有她这样有家庭背景的人才能够享用。他倔强的摇了摇头,赌气端起杯子,大口灌了下去。她瞪大眼睛,摇摇头:“你这种喝法,就象老牛喝药,浪费了我的茶了。”
他突然觉得自己受到了嘲笑,忿忿的走了。
但是从那天起,一切好像悄悄的在改变,她不再咯咯的傻笑,也不会直盯着他,逗他说话。偶尔目光掠过他的脸,常常会不由自主的面颊绯红。他更加沉默,低着头干活,只是在两人擦身而过时,被她的幽香撩的一阵阵心跳。
那个年代的政治风云,总是在和人开着各种玩笑。玩弄着人们的命运。
一场反右运动,无情地扼杀了朦胧中的胚芽。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他自告奋勇的带上了右派的帽子。为了顶替年过半百的总工,他又自告奋勇的申请下放到西部。
走的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人们的心里也阴阴的,沉沉的。没有人来送他,他独自一个人,拎着简单的行李。匆匆的走出厂门。
转过弯,树后一个哽咽的声音:“师傅”。他停住了脚步。
她红肿着双眼,神情惨然。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那么自然:“你不是总想看师傅笑么,师傅笑的不难看吧?”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似乎想扑过来抱住他。他伸手止住她:多保重吧,师傅走了!她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个装着茶的小袋:“带上它,想我的时候喝一杯,我会等你回来的。”
他接过来,骤然转身,没有说话,也不敢回头,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张口,自己就会放声大哭,只要一回头,自己就再也无法离开。忍着心碎,咬紧牙。快步离去。
四十年过去了。
在闹市区的一隅,一间小小的茶吧。每天的黄昏时分,总有一个耄耋老人,步履蹒跚的进来,坐在靠窗的桌旁,要一杯茶,慢慢的呷尽。然后久久地想着窗外的远方眺望。等到块打烊了,才会神情索然的离去。
一天又一天。终于有一天,这位老人没有出现。
病床前,他和她又见面了。他已行将油尽灯枯,她得到消息专程从大洋彼岸飞来。执手相看,泪眼朦胧,相顾无言。良久,他颤抖着从枕边拿出一包东西。她接过来,轻轻的打开,一个发黄的纸袋。里面是已经粘结的像石头一样硬的没有味道的茶叶。这是四十年前他们分手时她给他的。她泪雨滂沱,失声痛哭。他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他走得很安详。她以妻子的身份为他安排了后事。在他的灵前,摆放着那袋珍藏了四十多年的茶叶……
煮开一壶茶,只要几分钟,煮开一段爱情,却要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