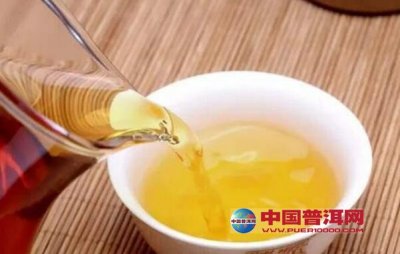我是一个很少抽烟的女子。但绝对是一个邋遢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的人。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忘记了洗脸刷牙。但一不小心遇上了你,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
更多的时间我愿意一个人默默的喝茶。什么都不想,可以什么都想。安静中,我有时做梦都想把自己变成淑女,变成琴棋书画什么都会的女子。
可想想,变成什么又能怎么呢?成为什么不是我的梦想,我只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在云南,出了喝茶,除了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外,我似乎再也找不到让我心动的事了。
我床下的方便面是一个叫冬瓜的男人买的。冬瓜不是名字,也不是外号,纯粹是因为冬韵,因为我们都是爱茶之人的那份情愫。
朋友段兄说:“在云南,真好——/不用写《出云南记》和《回云南记》/我就写这首《在云南记》/我就独守在云南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而我一直想写《最美云南记》,和段兄的思绪估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云南人,深深地爱着云南。
冬瓜是我朋友中喜茶超出自己生命的人。他以为,茶汤如母亲的奶汁一样,喂养着我们的生命,存在不是独一无二的,吃茶就是一种修行。
一不小心遇上你 冬瓜有时会来为我做饭,然后看着我吃完饭,他会为我泡大杯我喜欢的普洱茶。微微一笑地说,这个能减肥。所以我便一口喝下,即便我知道它是一个最美的谎言。
冬瓜说,青,我离开后,记得吃饭。如果饿了,不想做饭,床底下有你喜欢吃的方便面。
我不屑地说,走吧,走吧,有多远滚多远。
因为一杯茶,我和冬瓜相遇,而一杯冬柠普洱而际会。富有浪漫气息的名字。
曾经,冬瓜说,青,我们一起去经营一间茶吧吧,春夏秋冬都为你煮茶,然后陪你看日出月落。
我说,好啊。如此的生活就是我梦寐以求的。
他说,是啊,你可以写字、看书、听歌,而后和来来往往的客人聊天。听他们的故事。用你的笔记录下来,如此,简单快乐。
我说,如此真幸福,最主要有你陪伴。
如今,每天下午时,我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就一个劲地喝茶,茶喝到无味,人思到无期。
那时,冬瓜直直地看着我,我也瞪瞪地看着他,半响后,我们一口一杯茶,再哈哈大笑。最后,冬瓜会为我讲述他曾经在这个小城的故事。关于那些年的爱情,事业,路过生命里的那些人和事等。
看着冬瓜,感受玻璃窗外,温暖的阳光,西式的建筑,来来往往的人群,各式各样的打扮,不同的表情。无法揣摩的故事和结局,人间沧桑,人性从表到里。华丽虚伪的外表遮挡了扭曲发霉的灵魂。
世间太多东西,冬瓜说都不想去揣测和猜忌了,就想好好的活着。
我微微一笑说,我们要一起活着。
他说,如果把我写进我的小说,你想把我写成什么样呢?
我说,呃呃呃。我想写死。
他说,那就按照你的意愿吧。
冬瓜一次喝了大杯茶,而后很满足地望着我。眼眸里有太多难以揣测的情节。
昆明,这个美丽富有活力的城市,我总是在这里找不到半点的凭证。爱情也是如此。
冬瓜说,青,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我们就这样简单地听着音乐,回想你诗词的味道,慢慢悠悠地品尝着云南普洱茶。如此,生和死,喜怒哀乐,俗世的任何都和我们没有关系,我只想这样简单地看着你。不涉及任何俗世的水域。
看着可爱的冬瓜,我轻抿一口茶。从头到脚,内心至灵魂,彻底地清洗了一遍。我说,冬瓜,我要远行了,来年,如果我回来,我们再在一起品茶。
冬瓜说,非要离开吗?
我说,不,不是离开,是对感情的流放或者是融化。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个不适合长居在一个地方,我也不适合为谁守候。我是一支开在山崖的野百合,习惯了放养。
冬瓜说,我会等你,等你归来,我们一起喝茶发呆。
我微微一笑,来年,如果我们都安然无恙地活着,春暖花开时我带着马匹,青稞酒,马头琴、弯刀、明月来和你相约。
一不小心遇上你,茶韵到无至;心到至远,情到无涯。
(责任编辑:一凡)
|
 |
 |
|